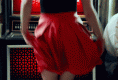放假啦,带上你的丝袜与灵魂去音乐节上撒个娇吧!
2009年,草莓音乐节创办,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举办了第一届,如今它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音乐节,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
2009年,张晓舟撰写了一篇评论,将草莓音乐节视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风向标。
如今,七年过去了,张天师已经是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导演着新一代年轻人撒娇的方式,草莓的舞台也越来越大。
明天开始,北京和上海的草莓音乐节即将开场。草莓们,是时候带上你们的丝袜与滚热的灵魂,去草地上撒个娇了!
通州北苑到运河文化广场的路上,黑车司机向我热情推荐草莓音乐节:“那儿吃草莓都不用钱!”
虽然那儿的黑心草莓其实一颗要一块钱,但当听到广播里盛放的那首披头士著名歌曲《永远的草莓田》(Strawberry Field Forever),你还是会忍不住买上一盒。
Strawberry Field是利物浦一个儿童救世军总部的名字,那儿可以吃糖、治病、游戏、唱歌,列侬小时候最爱跟着姑妈去。如今纽约中央公园东侧,靠近列侬故居所在的大厦的一小块空地,也被命名为Strawberry Field,专门辟出来纪念列侬。

你有无数种纪念约翰·列侬的方式,这会是最受欢迎的一种
我去过那儿,大厦门口站着两个保安,彬彬有礼地挡住狂热的朝圣者,笑容可掬地和朝圣者合影,仿佛自己成了列侬的替身。百米开外的那一块叫作草莓田的空地,似乎也充当了列侬故居的替代品,朝圣者可以在一个圆圈周围或在圆圈里面写字、献花、献烟、献巧克力,甚至献上大麻(不过要小心警察),献上贴着红色爱心标志的内裤,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自然会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替列侬收下阁下敬献的这些好东西。
然而,当一位头戴花圈的老嬉皮坐在地上,目中无人地兀自唱起列侬的《想象》,你身上恐怕还是会泛起一点鸡皮疙瘩,想起那被时光销蚀的,被死亡的血红印章所钦定的爱。草莓田,就是从儿童救世军到青年救世军,从儿童乐园到成人乐园。
说到嬉皮花童的成人乐园,想起《美国坎坷的一代》一书中描述伍德斯托克的一句话——“一代人去那儿相互问好”。
自从《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在“文革”后出版,伍德斯托克就成了中国知识青年的镜花水月。到了90年代末迷笛音乐节创办的时候,迷笛也就被媒体糊里糊涂地戴上了“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帽子,只不过迷笛的滚友未必了解伍德斯托克到底是个啥样,而在书上垂涎过伍德斯托克的知识分子却压根不会来迷笛。
想起当年的迷笛,就会想起左小祖咒电话里的破烂大嗓门:“你去伍德斯托克吗?!”我知道他没钱打车,是想蹭我的车去香山看迷笛。

左小祖咒在草莓,不知道是不是蹭天师的车去的
正因为我们不再年轻,也不再轻易热泪盈眶,但想起从前的迷笛,想起舌头乐队的《他们来了》或者木推瓜乐队的《悲剧的诞生》,还是会热血暗涌。那时候我们何止是去那儿相互问好,简直是相互拥抱,形同革命基友,连撒泡尿也要相约一起去,在希望的田野上,冲着西山的夕阳,齐刷刷拔出小鸡鸡,就像士兵拉枪栓一样整齐。
直到2003年,舌头解体,木推瓜解体,那一年国庆最后一次在迷笛音乐学校校内看迷笛音乐节,目睹爱国粪青群起攻击一支日本乐队,谩骂、起哄、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当我看见一个摇滚铁托买了一箱矿泉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舞台上的日本乐手,当我看见一个摇滚铁托一会儿跟着一拨人怒骂“小日本滚下来”,一会儿苦大仇深地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会儿又跟着另一拨人为日本乐队拼命鼓掌,我知道所谓铁托的时代该结束了,现在终于轮到一代人去那儿相互问候彼此的老妈了。我看见舌头的吉他手朱小龙狠狠踢了一个反日爱国摇滚义勇军粪青的屁股,而我转身走了。
那一次舌头乐队没有参加迷笛音乐,没有再演一次《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也没有来得及正式录下这首伟大的歌。舌头乐队随着这首挽歌分崩离析,一个时代似乎也随之分崩离析。对不起妈妈,我们没法一起飞一起摇滚,我们只能各自孤独地飞了,或者混进面目模糊的汹涌的人群。

舌头乐队这次也将登上北京&上海的草莓舞台
此后迷笛音乐节逐渐走向地上,再后来,摩登天空音乐节横空出世,并且又生出草莓音乐节这个“子品牌”,中国的音乐节开始井喷,虽然喷的大多不是油而只是自来水。而迷笛和摩登天空(兼草莓),在一些资深滚友眼中,似乎成了国家德比,从北京杀到上海又杀到镇江,搞得跟皇马巴萨似的。
得益的是那些知名乐队,他们在两大阵营之间跑来跑去,齐齐风光,来来回回都是这帮老面孔。中国摇滚和民谣仍然如此贫乏,如此同质化。然而迷笛和草莓各自的铁粉在豆瓣上的混战,却说明中国摇滚乐已经初步形成了品牌效应,尽管音乐节内容过于趋同,但各自的支持者也愿意捍卫彼此的摇滚战旗——尽管所谓战旗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logo而已。
迷笛似乎更受资深老炮的拥戴,尤其是那些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朝圣的滚友,迷笛是他们的延安。迷笛的口号应该是“一代人去那儿死磕”,死磕更代表了源远流长的早期摇滚铁血精神,而草莓音乐节的口号恐怕应该叫——“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撒娇”。
从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变成让我在草地上撒点娇。

南方的江山太娇媚,腐蚀了我的热血
不管是迷笛还是草莓,海魂衫和红领巾都招摇过市。迷笛依旧能看到大军靴,而草莓是匡威鞋和回力鞋的天下。草莓最重要的视觉标志当属丝袜。一个中年大老爷们在议论:“操,你说现在的姑娘怎么都不穿裤子!穿着袜子就跑出来了?”
穿裤袜不稀奇,稀奇的是裤袜的颜色:诡异的蓝、诡异的红、诡异的绿……晃得人像吃了迷幻药,如果真的吃了迷幻药,舞台两侧两颗巨大的草莓会恍然变成铁血地雷,但二十年前,他们还只是精子和卵子——精子们和卵子们去哪里相互问好呢?铁血已沦为草莓酱,胡涂乱抹在时代软绵绵发酵的新鲜面包上。

这里,你可以奇装异服,也可以…不穿衣服
草莓更嫩、更嗲、更小资、更文艺。摇滚乐和民谣文化充当的已不是大饼油条,而是零食,不是麻辣烫毛血旺,而是饭后的草莓冰激凌,这也见证了社会一步一步的宽松和自由,虽然可能仅仅是娱乐的宽松,以及恶搞的自由——比如“南城二哥”用饭岛爱调侃“淫奸会”的自由。
草莓音乐节是以小“阴蒂”(indie)为主小清新为辅,然而重口味的却并非金属舞台,而是像南城二哥这样欠扁的货。如果说子曰和二手玫瑰从前创造了一种相声摇滚,那么南城二哥就是披着摇滚外衣扮演下半身版郭德纲,其下三路很像春节地坛庙会上那些黄段子相声。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黄段子说明音乐节的确越来越向庙会看齐了,只不过音乐节的庙会有一个更小阴蒂的名字叫创意市集。
音乐节开始吸引了宝马和爱马仕这样的赞助商,有一个叫做love的爱舞台,居然在舞台正中央放了一辆宝马,周云蓬就在宝马前面唱《中国孩子》,而Carsick Cars则在宝马前面唱《广场》,草莓的气息在宝马和“淫奸会”,在爱马仕和饭岛爱之间飘扬。
汪峰老师没来,让信仰在空中飘扬的任务就落在唐朝身上。他们唱了《浪漫骑士》,丁武说这是献给父辈的歌,但80后90后原本就是为了反抗逃脱父辈的唠叨来这儿的,没想到听到父辈在这儿唠叨爷爷辈,而且是以重金属的名义唠叨。
这也是第一次,《国际歌》居然没有激起我任何感情,丁武早已飙不上去高音了,他只能把麦克风转向乐迷们,可合唱的却稀稀拉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懒得起来,他们坐在草坡上,看一个巨大的粉红气球冉冉升起,及时转移了阶级斗争的方向。《城市画报》的美女衷声抬头赞道:好萌啊!我问什么叫萌?她说萌就是萌。我一下明白了:所谓萌,就是在血脉贲张的《国际歌》中,一代新人乘着巨大的粉红气球远去。

唐朝乐队还能飙上高音吗?
唐朝的《国际歌》飞得既没有汪峰高,也没有90后的气球高。而在《二十四城记》这样一部地产商投资的电影中,贾樟柯竭力想注入某种社会意识,他特意拍了一帮工人在唱《国际歌》,可惜这是唯一通不过审查不得不剪去的镜头,因为在一个行将倒闭的工厂里唱《国际歌》,跟在草莓音乐节和宝马推广会唱《国际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唐朝后来确实曾在一个宝马的商业活动中高唱《国际歌》,没有比这更二的了。
不是信仰,而是信仰的胸毛,在空中飘扬。请问阁下捡到了几根?
但二十年前,唐朝的《太阳》曾令我热泪盈眶,他们应当是中国摇滚最早的励志天团。只是在励志天团纷纷被加速炮制以便跟成功学比翼齐飞的今日,他们成了奥特曼。而号称“华语乐坛第一励志天团”的那四位老师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励志是多么容易——只要你的歌够阳光却无锋芒,只要你的歌像无痛穿孔一样轻松,像耳环一样炫酷,那就有望排队成为励志天团。
草莓音乐节上不少乐队都在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草莓榨汁机,是一个弹性良好的摇滚蹦蹦床。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就一定比杨臣刚好吗?
音乐节每天七八个小时实在不容易打发,没有比在几万人的喧嚣中发呆更无聊的了,而我又不像那个叫黑刀的草莓音乐节搞手脸皮那么厚,他的工作就是举着相机逢美女就拍就搭讪。
幸好有创意市集帮你找到存在感。我可以去淘淘唱片来消磨时间,我淘到一张King Tuby,估计龙神道乐队也会喜欢;当我买了一套3CD的地下丝绒现场回来,赫然看到舞台上是一支港版地下丝绒,尤其是那个戴墨镜的酷哥像John Cale一样拉小提琴,那是移居北京的香港乐队“憬观:像同叠”;我还掏到Devo的现场版、Pere Ubu一张少见的CD(背面是DVD)、Clash的一个罕见版本。

重塑雕像的权利 贝司刘敏
我带着这些老炮去看“重塑雕像的权利”,他们俨然成为摩登天空厂牌的头号乐队。当这支后朋克病兽发作,当1977向2009呼救,当suicide、cage、police这样的词像尖刺一样逼近嫩白无辜的肌肤,你只能庆幸音乐节还有这么一点差不多是硕果仅存的铁血。他们既不健康也不励志,对死亡和对青春一样满怀爱意。
但更受欢迎的永远是空洞的美,是曹方的“比天空还远”或小娟的“山谷里的居民”,如果许巍是“爱如少年”,那么她们就是“爱如少女”,而远比她们年轻的王若琳反而唱出一点沧桑,但顶多也就是像诺拉·琼斯那样,中产阶级主流审慎的空洞。我淘到Marianne Faithfull 2004年的专辑,唱了很多P.J. Harvey和Nick Cave的歌,要知道这个嗓子如同缓缓打开的地狱酒窖大门的老太婆在王若琳这个年纪,还只是一颗60年代的小草莓。
一切都那么美好而空洞。刺猬乐队高唱“社会是伤害的比赛”,那么避免受伤的方式就是像刺猬一样把头缩起来,咬咬自己的手指,舔舔自己的羽毛,把摇滚乐内化为一个安全舒适的乐园。没错,伍德斯托克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我也只是精子和卵子。而四十年之后的今天,音乐节当然不可能再是乌托邦应许之地或社会发动机,它越来越像一个儿童乐园。
我看到创意市集潮水般涌来,包围乃至吞没了舞台,很多乐队就像在舞台上摆摊一样,兜售他们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小阴蒂。自由万岁,最后仅仅沦为自由消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
从通州运河广场回家的路上,我在728路公车上一路看劳动节电视晚会。一男一女用美声高歌,歌词只有两句:“我们的工厂,和谐天地;我们的小区,和谐天地!”又有一男一女也用美声高歌,歌词也只有两句:“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成龙也唱过的名曲《国家》。
这个国家,在《国家》和《永远的草莓田》之间,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9)
本文选自张晓舟的文化评论随笔集《死城漫游指南》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买

彩蛋
最后送上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当年玩乐队时唱的一首歌
如果你也听过
恭喜你
你和我老板一样老了
标签: 手淫早些能恢复吗 夫妻用品买什么 女性同房出血的原因 音乐节 草莓 乐队
文章来源:费洛蒙的情趣世界
文章链接:
版权所有 转载时必须以连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
- 微信访问,长按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我们
微信搜索公众号:费洛蒙的世界商城关注我们
- 微信访问,长按二维码添加微信客服
复制微信号:18002554425添加朋友